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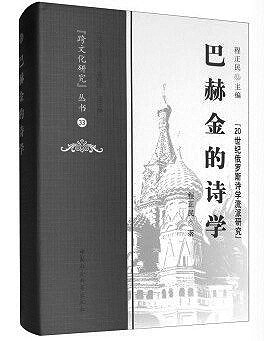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接洽中心“三老”程正民(右)、童庆炳(中)、李壮鹰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合影。
【述往】
学东说念主小传
程正民(1937—2024),福建厦门东说念主。1959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汉文系,留校在文艺表面组任教,老师文体概论课程。1965年调至苏联文体接洽所,曾任苏联文体接洽所副长处、《苏联文体》杂志常务副主编。1993年召回汉文系文艺表面教研室,曾任汉文系系主任。著有《20世纪俄苏文论》《巴赫金的诗学》《俄罗娴雅体新视角》等。
2月20日早上八点多,当程正民敦厚死亡的音问倏得传来时,我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那六合午就有新学期的第一次课,我得有所准备,但备课时期陆续跑神,研究程敦厚的一丝一滴蜂涌而来……
导读巴赫金
我知说念程敦厚的名字是1993年,但见到他本东说念主已是1999年。那一年,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在童庆炳敦厚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童敦厚打头阵,给我们开设了《文心雕龙》专题课;程敦厚则紧随其后,与另一位教授合开一门西方文论专题课。证实我的听课条记,程敦厚是2000年3月8日走上这门课的讲台的。他告诉我们,他的课是让人人细读苏联文艺表面家巴赫金的《陀想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他先讲两次,算是导读,接着是人人的自选动作:考中某章内容,细读一番,讲授出来。
说实在话,巴赫金的这本书我虽早已买到(购书日历是1993年12月),却一直躺在我的书架上睡大觉。跟着程敦厚的讲述,跟着对话、庄谐体、狂欢化、复调演义、狂欢式的天下感受等观点从他口中汩汩而出,我运行了对巴赫金的矜重阅读。因为头一学期听过童敦厚的课,我对两位敦厚的授课作风忍不住要阴暗比拟。比拟的抛弃是,如果说童敦厚主打慢慢悠悠,那么程敦厚则主打“大弦嘈嘈如急雨”,这种机关枪般的语速让我意志到,他不仅想维敏捷,而且照旧个急性子。他要是唱歌,揣测齐会嫌“一条小径曲曲弯弯细又长”节拍太慢,而是要换成“高洁梨花开遍了海角”的,为什么呢?因为《喀秋莎》是四二拍啊。
这就是我对程敦厚的领先印象。这种听觉效力,再加上阿谁精瘦、精干、精气神十足的视觉形象,更让我合计程敦厚活力四射。实践上,那时他六十有三,已退休在家,却被大他一岁的童敦厚拉入彼时刚刚报告顺利的熏陶部东说念主文社科重心接洽基地——文艺学接洽中心,成为退而束缚的专职接洽员,也成了童敦厚的左膀右臂。
话说2000年春天,我不仅细读了《陀想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全书,而且因为对第四章所论的“庄谐体”“梅尼普讥笑”“苏格拉底对话”深嗜深嗜颇浓,又决定把《拉伯雷接洽》也读起来,因为尽管前书也谈到了狂欢式和狂欢化,却仿佛是轻佻饰演,我想弄了了狂欢节、狂欢广场、狂欢式的天下感受是若何回事,便无法在《拉伯雷接洽》眼前绕说念而行,因为这本书中荫藏着这些问题的所有深邃。此书读毕,我专诚在书后写了几句,记载彼时的郁勃之情,其中一句是:“读此书时期,受到的冲击与升沉无与伦比。”亦然在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才终于写出程敦厚这门课的课程论文《民间话语的开掘与放大——论巴赫金的狂欢化表面》,此文不仅受到程敦厚好评,而且发表也流畅无阻,以致还得回了《异邦文体接洽》2002年优秀论文奖。现时想来,假如莫得程敦厚辅导,我能盘讲究底摸到《拉伯雷接洽》吗?巴赫金能在我心目中占据一个长久而困难的位置吗?
也恰是因为这本书,我才的确分解了一个情理情理:有些书是让你长学问的,有些书则是能深入你的灵魂的。于我而言,《拉伯雷接洽》昭着属于后者。
然而,直到程敦厚死亡的那天,我才从书架上取下他那本《巴赫金的诗学》,运行了对它的的确阅读。因为我确信,在一个东说念主在世之后阅读其著述文章,才是对他最好的担心。因为此次阅读,我才意志到程敦厚险些就是文如其东说念主:他的讲演是质朴的,刚健的,冗繁削尽的,直言不讳的,同期又是澄莹的,谨严的,条分缕析的,举重若轻的。经过他的清算、反想、索乞降归纳,巴赫金的全体诗学就既林林总总,又整齐齐整了。这本书出书于2019年,是他晚年的著述。从字里行间,我仿佛也晓悟到“庾信文章老更成”的风貌,精神不仅为之一震。更让我鼓吹的是,通经过敦厚的讲演,我不仅温习了一遍巴赫金,而且还发现了巴赫金“艺术的内在社会性”与德国粹者阿多诺“内在品评”之间的某种关联,同期,把它写成一篇论文的念头也在我心中潜滋暗长。
论从史出
程敦厚在总结我方的学术糊口时已经说过:“在20世纪俄罗斯各式诗学流派中,最困难的也最令我热爱的是巴赫金的诗学。”(《我所走过的学术说念路》)这话我信。在我的心目中,程敦厚固然写过《俄国作者创作脸色接洽》等书,天然是俄苏文论接洽人人,但这一人人的底色是巴赫金诗学。也就是说,假如莫得巴赫金这碗酒垫底,他的俄苏文论接洽是不是还能像现时这么丰润,有时就要打一个问号。
然而,直到程敦厚死亡之后我才发现,他的巴赫金接洽也恰是起步于给我们这届学生上课的世纪之交,因为那恰是他发表《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文体评述》2000年第1期)的时候,亦然钟敬文先生饱读吹他将此文“推广为一册书”的时候。于是才有了自后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书社2001年版),又有了在这本书基础上的拓展之作《巴赫金的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9年版)。当我意志到程敦厚是在“最好意思不外夕阳红”的季节才“咬定青山不质问”时,我对他的敬意又加多了几分。关于很多学者来说,年届花甲意味着收官阶段的运行,程敦厚却为我方规划了一个新的接洽来源。如斯志在沉又如斯壮心不已,岂肯不让东说念主敬佩?
连童敦厚齐佩服不已!铭记2013年12月26日,文艺学接洽中心像往年相通,开了一个年终总结会。会开至终末,童敦厚说:“我们要扎塌实实作念学问,要维持学术本位。你看我们的程敦厚,他就一径直洽巴赫金,接洽来接洽去,就成了这方面的人人。是以,你们要像程敦厚那样作念学问。”
程敦厚的学问作念得塌实,与他奉行“论从史出”研究,我就见他世俗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比如,2014年7月上旬,中心在京郊大觉寺开务虚会,谈及学科发展,童敦厚强调,以后的文体表面建立不应该再是大兵团作战了,而是要每东说念主接受我方感深嗜深嗜的问题,琢磨多年,然后再与名堂说合。轮到程敦厚发言,他则指出:“如何处理表面、历史和近况的关系,我们需要矜重接头一下。论从史出很困难,但如果不醉心近况接洽,也很难往前走。像别林斯基、巴赫金这种表面家, 首页-达昌奋香精有限公司其实齐口舌常关注文体现实问题的。”
动作一种接洽方法, 通河县嘉匹食用油有限公司“论从史出,民丰县和艾烹饪有限公司史论说合”天然开首关联着中国史学接洽的传统,但程敦厚之是以对此高度醉心,况且要与现实相说合,昭着与巴赫金脱不开研究。在《巴赫金的诗学》中,我就读到了这么的讲演:“从广义上讲,论从史出,任何表面问题必须回顾历史,通过历史接洽施展它的实质,施展它的发展端正。从文体史接洽的角度讲,文体史是要寻找文体的发展端正的,但端正不是编造编造的,端正是要从历史的接洽中得来的。”在另一处,程敦厚则径直指出:“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接洽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不行把文体接洽阻塞于文本之中,接洽文体不行脱离一个时期完整的文化语境,要把文体表面接洽同文化史接洽精良说合起来,唯有这么作念才气揭示文体创作的底蕴。”(《我所走过的学术说念路》)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论从史出”的强调。由此我也意志到,固然在晚年,童敦厚和程敦厚齐讲文化诗学,固然他们齐强调“历史文化语境”,但程敦厚所辩论的文化诗学中多出了一个“论从史出”,这是来自巴赫金的赠给。
由于程敦厚是巴赫金接洽人人,遭遇这方面的问题,我也时常向他请益。铭记2012年,我曾问他巴赫金是否用过“对话性杂语”(dialogic heteroglossia)。因为那时我正带着几位学生翻译好意思国粹者布莱斯勒的《文体品评:表面与实行导论》,其中的术语需要拿握准确。2017年,我向他求教哪种《巴赫金传》更值得一读,因为彼时我正在琢磨钱钟书的“暗想想”,想对钱钟书和巴赫金进行比拟。2022年正月,我去给程敦厚贺年,迎面问他“诗学”在俄语语境中有哪些解释,他立地取出一册《文体学导论》(北京大学出书社2006年版),翻到第196页,让我看作者哈利泽夫的说法。他还说:“我那本《巴赫金的诗学》不是送你了吗?我一运行就解释了诗学的三层含义,你且归不错望望。”我唯唯。
从程敦厚家出来,我忍不住惊叹:程敦厚可确切一册活字典啊。与此同期,童敦厚的一个说法也在我耳边响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乱点鸳鸯
查记载,童敦厚的这番话说在2009年3月11日。那六合午,中心成员开会,童敦厚说他准备卸任,要把中心主任交给李春青教授。谈及中心的东说念主员组成,他说:“我们现时的情况是‘三老’‘五中’‘五青’。三总是我一位,程敦厚一位,李壮鹰敦厚一位。俗语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这个人人庭现存‘三老’,那就是如有三宝了?”
实践上,李敦厚那时才六十有四,称“老”似不对适,的确的老东说念主唯有童敦厚和程敦厚。他们齐于1955年插足北师大汉文挂念书,又齐来自福建,也齐在大学时期崭露头角,最终成为留校东说念主选。所不同者在于,童敦厚其时在汉文一班,程敦厚在汉文四班;童敦厚提前一年毕业,程敦厚则是完成四年学业后平淡毕业,二东说念主遂由同学变为共事,同在汉文系文艺表面教研室任教。自后,童敦厚虽也被抽调到学校教务处干过,却基本上没离开过汉文系,而从1965年起,画框程敦厚转入苏联文体接洽所。直到1993年苏联文体接洽所终止,程敦厚才重回汉文系教书,在干过一届系主任(1995年—1997年)后,他就退休了。
程敦厚能回汉文系,童敦厚应该功不可没。
据李春青教授回忆,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程敦厚就成了童门弟子心目中的“副导师”,原因在于,那时候童敦厚已请程敦厚襄理作念课题、带学生,等于是拉他入伙了(《我的“副导师”程正民先生》)。“苏文所”终止后,程敦厚何去何从,本来是有些夷犹的,因为他也不错接受去外语系,但童敦厚但愿他“衣锦荣归”。在童敦厚的营救下,程敦厚不仅回到了汉文系,自后还被推到系主任的位置。
为什么童敦厚要请程敦厚回来?谜底其实并不复杂,我以为他是想找到一位给力的帮手。
话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童敦厚正准备厉兵秣马,大干一番。但阿谁时候,文艺学教研室青丁壮居多,他们固然朝气蕃昌,作念学问是一把好手,但一朝插足行政处理、学科研究层面,有时就显得教会不及。于是,寻找一位知根知底的知友一又友来为他出计较策、取长补短,就显得眉睫之内。这么,老同学程敦厚就成为最好东说念主选。因为他不仅虚心、低调、安适,而且脑子活,点子多,仿佛是“塔里点灯,层层孔明诸阁亮”。
铭记在庆祝程敦厚八十华诞的会议(“俄罗斯诗学发展新趋势”学术研讨会)上,罗钢教授发言时把童、程二敦厚比作《红楼梦》里的钗黛关系,说他们是“两峰对峙,双水分流”。我则在致辞中借用苏联学者普罗普《民间故事步地学》中的说法,把童敦厚看作“主角”,把程敦厚视为“帮手”。我说:“在一个故事中,主角天然困难,但如果莫得红娘的匡助,张生就娶不到崔莺莺;莫得少剑波的守护,杨子荣就打不进威虎山。不错说,在文艺学学科的建立中,恰是他们这对老搭档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才完成了文艺学的学科叙事,把我们这个学科带向了一个光辉时期。”
红娘是《西厢记》中的女二号,少剑波是《智取威虎山》中的守护长,这两出戏很多东说念主耳熏目染,是不需要解释的,需要解释的是普罗普的表面。在《民间故事步地学》中,普洛普归纳出七种变装——加害者、赠予者、匡助者、公主过甚父王、打法者、主东说念主公、假冒主东说念主公——它们涵盖了故事中的各色东说念主物。围绕着每一种变装又组成了一个“行为圈”,它们在故事中利用着不同的功能。在北师大文艺学书写出来的故事中,童敦厚天然是满盈的主角(主东说念主公),程敦厚则是无缺的帮手(匡助者)。他们要寻找的“公主”则是北师大文艺学的“顶层规划”,或者是童敦厚所说的,寻找“具有中国特质的文体表面”。在这种寻找中,程敦厚一直心甘宁愿地当着帮手、破裂、幕僚、绿叶,莫得涓滴怨言。这种变装意志不是走过场、作念神情,而是原原来本,心悦诚服,绝不磨叽。
在十五年傍边的时刻里,我亲目睹证了童、程二东说念主号称无缺的合营经过。我以致合计,无谓“乱点鸳鸯”来面容,就不及以抒发这种无缺度。
红泥小火炉
童敦厚死亡之后,我运行担任文艺学接洽中心主任。铭记“新官”上任之后,我第一次到程敦厚家中探望,他就讲起了我方当系主任的旧事:“其时是学校带领倏得找我言语,然后就把我‘逼’上了系主任的位置。当了主任后,我去探望了系里的几位老先生。因为其时汉文系矛盾多,情况复杂,我就跟钟敬文先生、启功先生颓靡,两位老先生言笑间就给我出了主意、想了办法。其实钟总是个理想主张者,他像堂吉诃德;启老则像哈姆雷特,他是一个怀疑主张者,天下就是由这两类东说念主组成的。这不是我的不雅点,屠格涅夫早就写过文章。当了主任就得职业情,职业情就要惹东说念主,但只消你是出于公心,又赢得了上头的营救,你就只管干下去。”连绵连续,旁求博考,三言两语,直指心窝,此谓程敦厚的言语作风。他在那边为人师表,仿佛是手把手教我若何当主任。
2017年6月14日晚上九点多,程敦厚给我打回电话。他启齿就说:“今天是童敦厚走了两年的日子,确切快!我想他了,专诚给你打个电话。”然后他又问我:“是不是会预料童敦厚,尤其是困难的时候?”我说:“是啊,因为我们既莫得童敦厚的颖悟,更莫得他多年酿成的那种威信。”于是程敦厚抚慰我,说:“你也挺阻挠易的。以后遇事多商量,轻松来,别火暴。”实践上,我当主任时期,恰是程敦厚意志到了我的“阻挠易”。固然这些话显得详细、缥缈,但毕竟亦然一种抚慰,仿佛在“晚来天欲雪”的时节来了一个“红泥小火炉”,让我感受到了融融暖意。
2018年10月20日,文艺学接洽中心驾驭的“文艺学新问题与文论教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在京举行,我请程敦厚致辞,他先是说了些面上的话,随后就转到我身上,说:“2011年在香山开会时赵勇刚买了辆新车,他开着车,把我和童敦厚送回了家。其时他是生人,车技一般,人人还不若何敢坐他的车。七年之后他已是一个老司机了,坐他的车妥妥的。”程敦厚说罢,底下即是一派笑声和掌声。
我知说念这是他在为我饱读劲加油,于是坐窝跟进一句:“谢谢程敦厚!”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是在2002年。20多年之后,答辩委员会其他委员的臧否之词泰半齐已忘却,但程敦厚的一个说法我依然水流花落。他说:“赵勇这篇论文能拎起来,不像有些同学写得比拟散。他的论题是《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派系的大众文化表面》,他索求出了‘整合’与‘颠覆’这两套话语,这就拎起来了。”
按我相识,“能拎起来”就意味着论文有了中枢命意。阿谁命意就仿佛一个抓手,不错放开,四面出击;能够兼并,万取一收。“拎不起来”的论文不一定就写得差,那内部也有散金碎玉,仅仅还莫得真金不怕火成块,塑成形。究其因,要么可能是材料不外关,要么就是方法有问题。我不敢说我的论文有多好,但好歹是有个抓手的;这个抓手是金镶玉照旧铁家伙倒在其次。我能意志到这少许,全凭程敦厚的那次辅导,是他为我这篇论文的重量过了秤,命了名。他的说法尽管很朴素也很家常,莫得“填补了……空缺”之类的赞词,但我可爱。自后,我之是以对一些诸如《萨特介入表面接洽》《巴特结构主张想想接洽》的博士论文有微词,提意见,即是因为这些题目唯有讲演范畴,莫得中枢不雅点。用程敦厚的话说,就是“莫得抓手,拎不起来”。如若用古文来说,最合意的句子应该是“无帅之兵,谓之乌合”。
尽管程敦厚的论文批阅给我留住了深入印象,但自后在很多年里,我仅仅出了书送上,请他雅正,并不敢敷衍写出什么文章就让他看。情理情理很简便,一是他年级已高,二是他手头的活儿也不少,我不行占用他的有限元气心灵和珍爱时刻。
然而,亦然从童敦厚死亡之后,我又运行让程敦厚审阅我的文章了。为什么我要让他受累?因为我在论文写稿之余,也频频写一些触及北师大东说念主和事的翰墨,于是就有了让程敦厚望望的念头,因为他既不错指出写法利害,也不错辩认事实真伪,以致还不错给我提供一些细节材料。于是频频初稿既成,我便打印出来呈他审阅。世俗三两天之后,程敦厚的“评审意见”就能到位。天然,我敢频繁打搅他,亦然因为那些翰墨并非什么高头讲章,不错让他消愁破闷。尤其是自后得知程敦厚可爱读这路文章之后,我就更是莫得脸色背负了。
现时想来,这些年我陆续请程敦厚批作文、提意见,所图者何?应该莫得什么功利标的,以致也不图程敦厚的表扬。我好像合计,每当写到北师大汉文系传奇中的东说念主和事时,我方只可从故纸堆中寻找尊府,而程敦厚是现场目睹者,我需要请他把关、考据,指破迷团。唯有这么,我所回到的阿谁历史语境——亦即他与童敦厚齐反复强调的阿谁东西——才不至于太详细、太骨感,而是有了那么点血肉丰润的滋味。程敦厚也碰巧心胸怜惜,肚里有料,于是他的评点频频恰到公正,他的提议时常切中肯綮。这种见教是如斯困难,以至于我自后以致合计,唯有经他过目、被我再改之后,文章才拿得动手,不然,我心里就不褂讪。
频频预料再也不行向程敦厚请益,我以后只可“文责景观”时,便不禁心中悲哀,有了一种“我有疑难可问谁”的荒僻。因此,关于很多东说念主来说,程敦厚的离世,是失去了一位贤明的师者、优容的父老,但于我而言,除此除外,照旧一位关切而严谨的文章把关东说念主远去了。
(作者:赵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体院教授)
本疆域片由作者及程正民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体所接洽员程凯提供画框


